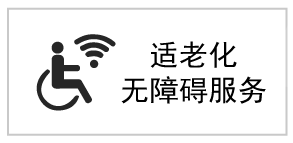区审计局:历史上的审计小故事“徽州丝绢案”——读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审计启发
马伯庸的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一书中详细描述了“徽州丝绢案”始末,作者通过查阅大量史实,生动的为读者还原了明代的一段真实历史,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帅嘉谟偶然发现徽州历年税粮账册中的疑点,逐步抽丝剥茧,寻丝觅迹,纠错证实的故事。徽州丝绢案故事背景虽远在明代,但帅嘉谟在查案过程中反复查阅账册、熟悉政策、重新计算、纠错证实的故事,引发了我一个现代基层审计人的共鸣,略有启发。
一个数字差异揪出大案
徽州丝绢案爆发后,引起徽州六县大辩论,动静不小。这起因却是账册中一个小小的数字差异。帅嘉谟在查阅徽州的税粮账册时,发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,除正税之外,还有一笔科目叫作“人丁丝绢”,须以实物缴纳,且数额颇大,每年要缴纳8780匹生绢。徽州府下诸县分账,六县中五县都没有“人丁丝绢”这一笔支出。歙县独交的8780匹生绢引起了他的关注,他进一步在《徽州府志》中发现线索,在“乙巳改科”时,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,480石,以“夏税生丝”为名义补之,折8780匹生绢。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,不知为何,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。经查阅相关典籍,便将此情况书写条陈呈文应天巡抚。
保持职业敏感,方能发现审计疑点。主人公帅嘉谟在查阅账册过程中,对这一小小的数字差异高度敏感,从而逐步深入发现疑点。作为基层审计人员,对被审计单位提供资料、数据要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态度,善于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,审查时要严谨细致、精心筛选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和疑点。随着时代科技进步,我们现在拥有了大数据分析等手段,在保持审计职业敏感度的前提下,科技助力,从珠丝马迹中发现审计问题的能力定会有所提高。
追根溯源还原事实真相。
帅嘉谟进一步追溯此项税收来源,发现国初六县均输 “夏税生丝”,就是歙县独输的“人丁丝绢”,但如今这个科目却被改成“人丁丝绢”,这是怎么回事?经他进一步调查,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,明白写着“坐取徽州人丁丝绢”。但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,用的名目是“夏税生丝”,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“夏税生丝”科目,因此地方不觉有异,上交至徽州府。徽州府向上递交时,悄悄从“夏税生丝”抽出应有的科目,划归到“人丁丝绢”之下。“人丁丝绢”这只鸡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占了“夏税生丝”的巢。到此,事情清楚明了。
抽丝剥茧,还原事情真相。在基层审计过程中,我们同样面临数据繁多、信息缺乏明显关联的情况,只有层层抽丝剥茧,追根溯源,清楚事情流程,通过关联数据按图索骥,才能厘清逻辑链条,拨开迷雾还原真相。
政策解读引发各县争论。
钱粮税赋,历来都是民政实务重中之重。此案几经呈报,便引发涉及诸县解释争论。各方要求查阅黄册时(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税赋档案),却意外发现关键信息缺失。对于政策的争论关键点便集中在《大明会典》有关条目上。《大明会典》徽州府条目下,只是提及由徽州府承担“人丁丝绢”,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。帅嘉谟认为这根本不合理,顺天八府,也有“人丁丝绢”税种,皆为诸县分摊,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,只是因为“人丁丝绢”被人篡改成了“夏税生丝”,以致五县之税独落歙县头上。然而辩论者陈嘉策表示,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,同样举出种种独征例子。诸县一时争论不下,报请户部裁夺,几经周折最终“均平”。
精准把握政策,促进精准落实。随着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,像故事中明朝官员关于政策解读“打口水仗”的情形已鲜有发生。但作为基层审计人员,我们常面临审计问题如何更加精准定性的问题,精准把握国家政策法规显得尤为重要,在法律法规及重大政策的把握解读上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,同时要紧跟法律法规的变化,切实提高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。